南外语文特级教师谢嗣极谈语文学习的远功和近
语文学习的近利
不可否认,这个时代人们并不讳言追求功利,学生,学习语文没有不希望考高分的,所以我先讲近利,所谓近利就是大大小小的考试考出好成绩。
为了应试,家长会给孩子买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书,各种试题集、应试指导用书和课文配套的参考资料。这类书我主张少看,尤其在初中或高中的起始年级不宜做中考、高考模拟试卷。我主张,订一份《咬文嚼字》,帮助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。文言文要熟读成诵,增强语感,古诗要尽量背诵,可以读一些通俗晚懂的,高质量的诗歌讲解与赏析的书,比如莫砺锋的《莫砺锋说唐诗》。课上要积极思考,不可只记教师给的结论。
考试,学生最感困难的是现代文阅读和作文。现代文阅读,别说学生觉得难,就是我们老师也觉得难。不是有作者自己做不出拿他们的文章命的题吗?这不奇怪。题目不是做得越多越好,要适量。题目做多了,题目若不科学,适得其反。
还得讲一讲语文的作业,经常有家长提老师的意见,说作业布置太少,这里的作业主要指与课本相对应的所谓课课练。其实,语文作业,在我看来应该是五类:练字,在低年级的时候就把字练好。写作,随笔和作文,随笔重自由表达,作文有一定的训练目标。背诵,背一定量的文质兼美的诗文,对背诵,人们一直有一种偏见,认为是死记硬背。年轻时背点东西,是终身受用的,现在背得太少,背得有价值的东西更少。读书,读自己感兴趣的书。适当的应试训练,所谓适当,是指要适时,要适量。如果读书多,上课又积极思考,有一个学期训练,最多一年训练足够了,家长们,不要再给孩子做各种各样的课课练,不要反对孩子读书。
语文学习的远功
所谓远功,即终身受用的语文学习。包含两层意思,一是语文学习终身受用,这受用不仅是功利的用,比如写个总结报告,写篇学科论文等,还包括无用之用;二是语文学习是伴随终身的。
㈠自由读书而不是做大量习题。
我主张把初中三年、高中三年,分为五加一,就是五个学期加一个学期,五个学期用来自由读书,一个学期用来应试;至多二加一,两年时间用来自由读书,一年时间用来应试。打个比方,语文学习,读书与应试的关系,好比习武,是内功与招式的关系,内功练好了,随便练什么门派的武,上手都快,内功不够,光有招式,只是花拳绣脚,没有力量。
学习越困难的学生越应该多读书,这话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:“学生学习越感到困难,他在脑力劳动中遇到的困难越多,他就越需要阅读:正像感光度差的照相底片需要较长时间的曝光一样,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头脑也需要科学知识之光给以更鲜明、更长久的照耀。不要靠补课,也不要靠没完没了的“拉一把”,而要靠阅读、阅读、再阅读,——正是这一点在“学习困难的”学生的脑力劳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”[①]
多读书,先别问有什么用。语文学习是个慢活,如同吃饭长身高,如果你吃了一学期的饭,量一量未见长高,于是得出结论:吃饭对长身高没用,于是不吃,吃增高药,穿增高鞋,结果只有一个。如果你坚持每天吃饭,某一天,你忽然发现自己长高了不少。
多读书,其实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多,但是真正到了现实中,实行起来颇不容易,首先是觉得没有时间读书,学生作业太多,家长工作太忙。比如,孩子如果成绩不好了,还想读点课外书的话,可能家长和教师都会反对。典型的例子是黄永玉,他成绩不好,老留级,“初中三年总共六学期,我留了五次级”。他偏科,“数、理、化、英文,费那么多脑子去记,而我长大了肯定用不上”。他旷课,不务正业,“一开学,我就把领来的新书卖了,换钱买袜子、肥皂。一头钻进图书馆去,懂的也看,不懂的也看。” 今天的眼光看,他简直就是一个差生。
他说:“一开学,我便把领来的新书卖了,换钱买袜子、肥皂。一头钻进图书馆去,懂的也看,不懂的也看。”
她管图书的婶婶骂他:“书读成这副样子!留这么多级!你每回还有脸借这么多书,不觉得羞耻?”[②]
家长要有淡定的心态。孩子如果有几次都得不好,家长就不淡定了,如果这一次排名比上一次落后了,就找老师,我孩子退步了,退步这话很不科学,孩子每天都会学到一点新东西,怎么会退步呢?所以不要问题横向比,要纵向比。这话家长会不同意,升学考试是选拔,是横向比,我怎么能纵向比呢?不是有三年嘛?所以我主张把三年分为五加一或二加一啊。家长一不淡定,就怪孩子,就加大练习,甚至找家教,孩子自由读书和思考的时间被压缩了。各个孩子的情况不同,只有给孩子自由,他的学习才有针对性。
先贤们喜劝人读书,留下了许多劝读的名言:开卷有益。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书到用时方恨少。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在中国谁不能背几句关于读书的名言?其实看看这些名言,都是从“功利”的角度劝人读书的。如果有一天,读书没有功利的作用了,也就不读书了,所以,中国经常流行读书无用论。
读书不应为了功利。我认为读书如同呼吸,其意义在于生命的需要。如果这样,那么读书就是自然而然的事,读书时,也不会觉得我正在读书了。谁在呼吸时觉得我在呼吸了呢?只有一个生命垂危的人,才觉得呼吸的重要,才要靠外力来促使呼吸。由此看来,到了要提倡读书的时候,情况已经不妙了。当然,不妙了不能任其不妙下去,就得有人来提倡,直到读书成为自然而然的事;就如同呼吸困难了,就要借助机械,直到恢复正常呼吸,不然生命就有危险。
懂得读书真谛的人,读书决不仅为了某种功利;或者说仅为某种功利而读书,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读书。叶圣陶先生说:“一些古书,培育着咱们的祖先,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,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,才不至于无本。若讲实用,似乎是没有,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了;可是有无用之用。这可以打个比方。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,道路几千,跑上峨眉金顶看日出,或者跑到甘肃看敦煌,看石窟历代的造像跟壁画。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,他们干的完全没有实用,只有那股傻劲儿倒可以佩服。可是他们从金顶下来,打敦煌回转,胸襟扩大了,眼光深远了,虽然还是各做他们的事儿,却有了一种精神。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。”赫尔曼·塞黑说:“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这种或那种能力和本领,而在于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,正确认识过去,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未来。”这也是无用之用的意思,可见中外对此有共识。
读什么书?这是人们常问的问题,或者说常感困惑的问题。
据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介绍,目前,我国年出版图书世界第一、日报发行量世界第一、电子出版物总量世界第二、印刷业总产值世界第三,出版大国名副其实。特别是数字出版,从无到有,逐步发展壮大,2011年总销售额已达1377亿元。一年出这么多书,读什么确实是个大问题。
因此,总有人希望别人推荐,也总有人喜欢给别人推荐,如果推荐得好,按别人推荐的读,不失为一种捷径,但是恐怕不太靠谱。这要看你为什么读书,要靠自己在阅读读中选择。
黄苗子认为读书应分两种类型:
一种是消遣、陶情养性,暇日或清闲时一卷在手,悠哉游哉地读。例如《庄子》,鲁迅、郁达夫的散文,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,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……当然历代名家的诗词文集,以至于新出的杂志,都可以这种心情和态度去读,读时随手翻阅,遇到合自己心意或自己想到而书中更深透地说出来的话,其乐无穷。这样读书,既可陶冶性灵,亦可深受教益。
另一种是专家或研究性的书,为了工作或教学需要,对某一种学术,必须作深入的钻石,得字斟句酌去钻、去想。这种实用性的读书,作为研钻家肯定深有兴趣,但一般人勉强去“死记硬背”,则颇乏味。[③]
我以为,我们学生则两种书都要读,陶冶性情的书当然要读,我们学生现在虽然还暂时不是专家,不要为工人需要去深入钻研某一种书,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看一些应试的书,只不过我们看应试的书不能过量,这一点等会详说,现在先说说自由读书,读些陶情养性的书。虽然我无力给大家推荐陶冶性情的书,但我以为读书要有两个标准:
读什么书,有两个标准:给人积极、乐观、向上、向善的书,不过“积极、乐观、向上、向善”关键还在看得人如何。比如一部《资治通鉴》,编著的目的是“鉴前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”,宋神宗甚至认为这部书,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,应该说是一部传播正能量的书了吧,可是有一天我看闲书,看到一句“一部《资治通鉴》,实际上也是一部资乱通鉴”,这话说得太对了,为什么目的和效果会相反呢?全看读书人的品德修养。所以,读书先要提高人的修养,当然读书也可以陶冶情操,提高修养。
语言规范充满智慧的书。现在写书的人很多,不少书,甚至有些名头很响的学者写的书,语言粗制滥造的不少,比如的一本杂志叫《咬文嚼字》,经常咬一些名人书中的错误,汉字、汉语太复杂,有错在所难免,但要尽量避免。中学生读这样的书对学生规范用语不利,所以我主张读语言规范的书。
读什么书?有两个路径。最简便的方法是以语文课本为起点,比如,课本上选了《神的一滴》,这是节选自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,你可以把《瓦尔登湖》找来看看,还选了《最后的常春藤叶》,这是欧·亨利的小说,你可以把《欧·亨利短篇小说集》找来看看。只要有兴趣,做有心人,自然会根据自己的趣味选择读哪些书。
陈乐民的《书巢漫笔》,其中《读书的“连环套”》一文云:
“读书无止境。就是划一个范围,也不能把属于圈定范围的书通通看过。
最近要考虑《西方外交思想史》的绪论,便找些书来看。看了老友李元明遗作中的一些章节,立即觉得‘套’着古代史,中古时期有些问题又‘套’着国别史。例如,英法百年战争‘套’着英、法两国的历史;法兰克‘套’着日尔曼、神圣罗马帝国;宗教战争‘套’着宗教史,等等。
本想看看门罗主义,结果上引出华盛顿,下引出林肯……而美国独立战争又联着欧洲战争,联着英、法、美一个‘三角’,联着俄国等宣布‘中立’的国家。”
然后又“套”出了《美国外交史》、《君主论》、《美国史》,最后他总结道:
“于是每一本书里都藏着许许多多的环子,都‘套’在另外的书上。每一本书好像都是一套索引,引出各式各样的书来。
读书的乐趣就正在这‘连环套’里。‘吾将上下而求索’。不求索也就没有味道了。”
陈先生讲的读书的连环套,一般的读书人也有这样的体会。陈先生讲的还只是书套书,其实这种“连环套”,不仅书套书,还书套人,人套人,人套书。套中有套。比如学了《林代黛玉进贾府》,你去读《红楼梦》,然后有兴趣再看看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书,可能会套出《红楼梦悟》、《红楼梦哲学笔记》《红楼梦人物谈》、《红楼梦人物论》等一系列的书。假如你读了《红楼梦悟》,觉得写得好,对作者刘再复有兴趣,于是找刘再复的书来读,你还会发现《人论二十五种》《师友纪事》,看了他的《师友纪事》,你对其中写到的人,如聂绀弩、李泽厚、范用等有兴趣,你会再找他们的书来看。这又是人套出书。读书的时间从哪里来?平时用零碎的时间读点篇幅短小的书,假期用整块的时间读点大部头的书。
㈡独立思考而不是背现成答案
读书,你会发现,对同一问题的说法,不同的书不一样,如读了《论语》里的一些选段,对《论语》有兴趣,你去找翻译或讲解《论语》的书,你会发现,有杨伯峻的《论语译注》、李泽厚的《论语今读》、钱穆的《论语新解》、还有南怀瑾的《论语别裁》。举大家熟悉的“朽木不可雕也”一段为例:
宰予昼寝。子曰:“朽木不可雕也,粪土之墙不可圬也;于予与何诛。”
李泽后翻译成“宰我白天睡大觉。孔子说:‘腐烂的木头没法雕刻,粪土的墙壁没法粉刷,对宰我,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?!”
李泽厚在后面加了记:宰予即宰我,孔门著名大弟子,以会说话见称,看来,宰我是个聪明而不够勤奋的、有才华而不重修养的学生,多次受到孔子的严厉责备。但孔子不但宽容收留他,而且还盛赞过他。不拘一格识人才,才可能是导师或领袖。
钱穆的翻译大同小异,只是最后一句译成了“我对宰予,还能有什么责备呀!”但他对这段话表示怀疑:宰予预于孔门之四科(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),与子贡齐名,亦孔门高第弟子。此章孔子责之已甚,甚为可疑。他认为这恐怕不是“当时实录”,但不能肯定。
南怀瑾对这句话给出了全新的解释,他认为,宰予身体不好,就好像是一根木头,内部本来就已经朽坏了,“粪土之墙,经蚂蚁、土狗等爬松了的泥巴墙,它本身便是不牢固的,会倒的,这种里面不牢的墙,外表粉刷得再漂亮也没有用”,宰予身体不好,他要睡个懒觉就让他睡吧,对他何必要求太过呢?
南怀瑾推崇《论语》,他有两个基本观念: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,天天要吃,研究孔孟思想必需从《论语》入手;《论语》是不可分开的,《论语》20篇,每篇都是一篇文章。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,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,这是不可以圈断的。再说整个20篇《论语》连起来,是一篇整文章。
陈乐民则认为,若把儒学当作一门中国哲学,《论语》担不起这个任务。它更像一本格言汇编,是教人怎样做人的。里面还有许多实在没有什么意义的话。就是一大盆“拼盘儿”,没有像南怀瑾说得那么神圣。
还有一个叫金克木的,他在蹭课的时候遇到了法国教授邵可侣,并且搬到他家里住,因帮他整理和校对《大学初级法文》,名字进了序文中,被陈世骧推荐到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法文。一个没有文凭的旁听生,就这样进了高等学府教起了法文。他把《论语》说得更玄,他说《论语》是一部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小说。虽是两千几百年以前的作品,但恐怕要到公元二千年以后才有可能逐渐被人真正认识。
到底谁说得对呢?需要独立思考。让思考成为一种习惯,读书常常见别人的奇思妙想,于是感叹:他是怎么想到的?怎么想到的?有思考的习惯。
思考,不要放过社生活中的各种小事。小事中往往人情世故在。以前老人上公交,一刷卡,会响起一声“老人卡”,听了终觉得有点不对劲,现在的声音变成了“您好”了,这一小小的变化传出的是什么呢?
还是交通工具,那个黄色的座椅上,有的标的是“老弱病残孕专座”,有的标的是“爱心座”,哪一种标法好呢?体现了什么样的人性关怀呢?
思考,也要从学习课文开始。庖丁向文惠君解了他解牛的过程:臣始解牛之时,所见无非牛者。三年之后未尚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,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。还解释他的刀用了十九年,还如同刚磨的一样: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,以无厚入有间,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文惠君听后感叹:吾闻庖丁之言,得养生焉。文惠君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,他从文惠君的话中得到了养生之道,那么,再想一想,还可以得到什么呢?外交之道,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,是不是也可以从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呢?治国之道,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,是不是也可以从庖丁解牛的故事中获得启发呢?
㈢自主表达而不是人云亦云
表达有口头的和书面的。学生课上参与讨论,就是很好的口头表达的训练。鼓励你们的孩子积极参与课堂讨论。课堂参与有两种,一种是提出疑问,一种是发表观点。我国学生不敢问,也不善问,所以有人说,我们的课堂缺“问”,要鼓励孩子提出问题。还有一种是要鼓励孩子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,不要怕出错。在这一点上,我们要向我们讨厌的日本人学习,日本人的观念是,“课堂就是出错的地方”。要不怕出错,也要通容错。
培养口头表达能力,看要以看一些演讲的书,如《最伟大的演说词》。
第二是书面的表达,就是写作,一般学校要求学生的写作有两种,一种是课堂作文,一种是随笔,前面讲过,随笔是纯自由的写作,课堂作文,应该一次有一个训练的目标。
钱穆有一次以“今日的午饭”为题,让学生作文,一学生文章结尾有一句“今天的午饭,吃红烧猪肉,味道很好,可惜咸了些”。这一句得到钱穆的欣赏。就这么一句话好在哪里呢?我们不是也会说吗?钱穆以此为例告诉学生,说话须有曲折。
下面是王力写的一段文字:
“薪水”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,意思是说,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,只够你买薪买水。但是在抗战了七年的今日,“薪水”二字真是名符其实了——如果说名不符实的话,那就是反了过来,名为薪水,实则不够买薪买水。长此以往,我建议把“薪水”改称为“茶水”,因为茶叶可多可少,我们现在的俸钱还买得起。等到连茶叶都买不起的时候,我又将提议改称为“风水”,因为除了喝开水之外,只好喝喝西北风! [④]
这段文字写得多么漂亮!也许有人想,他是王和力,我又不是王力,那么看看我的学生朱煜冬的几则随笔:
终于上车了,找了个后排的位子坐下,窗上朦朦胧胧的什么都看不清楚,只有模模糊糊的车灯路灯霓虹灯交相辉映的大团光。
忽然觉得下雨的晚上的公交像一座城堡,或者说像诺亚方舟,一路横冲直撞乘风破浪。一瞬间,觉得那些表情或冷漠或困顿的乘客,都是这个世界的幸存者。
有时忽然想到些什么,不写下来过一会儿就忘了,所谓转瞬即逝的灵感啊。
看自己从前的某些随笔会陷入猥琐的自我陶醉中无法自拔:我到底是怎么从一个话题飞快地联想并切换到另一个话题上去的?感觉自己异常的神,但同时也知道让我再写一遍是写不出来的……有点悲伤。
所以说,若想写好随笔类文章而又没有钱钟书那种无比强大的记忆力的话,不停地写是唯一的出路。
这几则随笔不仅文字写得好,她的写作体会对同龄人也有启发作用。
乱七八糟说了一通,不过也算切合“语文学习杂谈”这个题目。
[①]苏霍姆林斯基《给教师的建议》第51-52页(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2版)
[②]黄永玉《火里凤凰》第111页(文汇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)
[③]黄苗子《书虫小札》第7页(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第1版)
[④]王力《龙虫并雕琐语》第109页(商务印书馆2002年12月第1版)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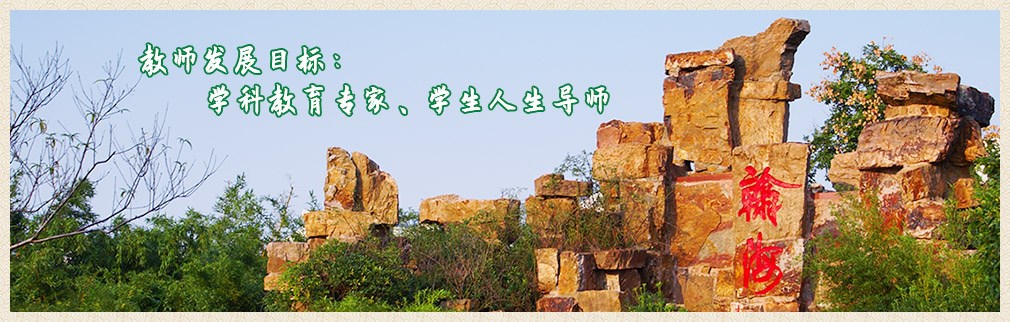




用户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